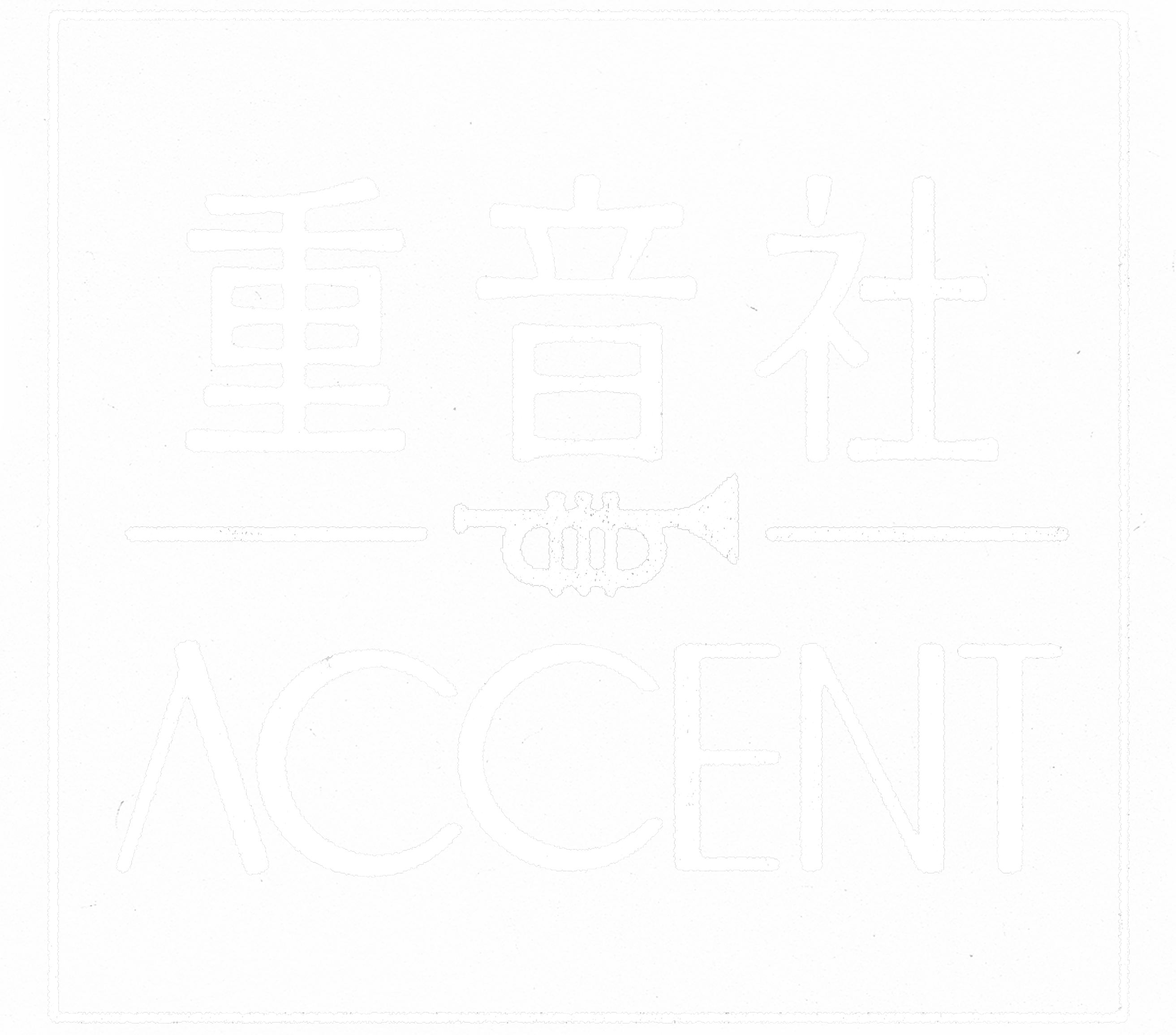王炜:没有世界的世界主义者
![]()
《一个叙事诗人的练习册》之二:《山河概述》
《山河概述》这首诗受2021年上海双年展(主题为“水体”)的文集《流》邀请而写,也是组诗《一个叙事诗人的练习册》中的第二首诗。《一个叙事诗人的练习册》由五首诗组成:1、《报信人》;2、《山河概述》;3、《一个少数民族人可以续写<唐·璜>吗?》;4、《一个执迷于“中国的终结”的人》;5、《结语》
我遇见个古怪的前江河学家,在成都
当他的所作所为都被忘记后的某一天。
我记下了他的一番话,不知道是
喝多了还是老之将至,使他健谈。
“我反对你们”,他说:“我拒绝接受
你们那种用地理学来夸夸其谈的方式。
你们议论河流、水电站和运输史
让大脑成为一个词语的堰塞湖
只为了杜撰一首约翰·阿什贝利
《在黄昏弥漫的天空中》那样的诗。”①
“可是,当你们在西南深处,走进
一片片麻布状,大炼钢铁留下的
灌木林时,难道丝毫不会想到
这片山地就是你们的反对者,当你们
走进地理学,就是走进否定性吗?
可是,每条水库化的河流,每个
风化的工厂社区,都不能反对你们。
你们博闻强识,早就把你们的自我膨胀
给专业化了。你们,年轻的专业主义者
总能够抢先一步,让我这样的人——让我
这种反对你们的失败现实主义者显得愚蠢。”
“所以,愚蠢,就是我反对你们的方式。
我并非在强调,我与你们的区别
我是在提醒我们的共同点。在所有
关于新旧、进步和相关知识的争论中
从来没有被说清楚的是,我和你们
都是以怎样的方式,站在了愚蠢的一边。”
他看了看我,见我愿意
听下去而非厌恶,便继续说:
“真的,愚蠢就是我们的来源。
我没和你谈论哲学,我以事实为证。
你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
出现在长江上的一种球形橡皮船吗?”
我连忙说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位
与其说是徐霞客风格,不如说是
敏希豪生男爵派头的先生已抢先
让我显得愚蠢。我诚恳表示谦逊
洗耳恭听,故事也的确奇妙动听
关于长漂时代,被遗忘的愚人船。②
“可悲啊,呜呼哉!”,仿佛在
背诵《蜀道难》,他正式开始说:
“那些大儿童们,以为只用胶水
即可修补,被长江撕开的橡皮筏。
又异想天开,发明了一种密封的
球状橡皮船,他们想象,它会在
激流中皮球一样蹦跳,渡过险滩。”
“可是,橡皮球里的人们在彼此的
呕吐物中上下翻滚。然后这只球
像塑料袋一样,被长江轻轻撕开。
里面的人尸骨无存。在那场被国家主义
背书的漂流竞赛里,球形橡皮船成了
长江的足球,这是谁的世界杯呢?”
“可是,正是这场在长江上游的滑稽
又悲惨的翻滚,成为一代人经验的缩影。
不,是经验的反像!是死亡留在
如今我们已知的经验知识背后的鬼脸!
我被它改变了,不能够再学习新知识
新语言、新的未来,从而度过与它和解
而非对抗的余生。它截停了我这代人冲出
亚洲,走向世界的欲望。你以为,你年轻
就没有一只沉默的鬼球,在你背后轻跳吗?”
“接受它吧。接受它,就是接受一种固有的
反成功性。你看,它在指点你看,那毁碎的
西南江源地区,就是国家主义大地的反像。
难道,这些年,我们不是继续置身于一个个
自己靠自己的球体,度过泥石流、水库危机
和地震,有时,让我们的理解一步就跨越到了
地理学的终结——一个地理黑洞吗?接受
这个地理黑洞吧。这是我们的知识、我们的
经济社会运作史,全部在其中坍缩的地理黑洞。
也是你我的生命共陷其中的地理黑洞。如果你
接受它,就请停止你从人文知识中派生的
地理想象,就此去摸索一种废墟制图学吧!”
我没料到,他从那只阴森森的怪球,立刻跳向
一个宏大话题。如各位所知,宏大话题是我国
特色的土锤表达方式。接下来的一切让我感到
我也在一只语言的黑暗球体中翻滚,在时间的
乱流中,没有从前,没有八十年代,没有以后。
“地理黑洞就是思想禁区。那些
濒危区和无人区,就是思想禁区。
我们真的理解它们,而且从此理解
半个世纪以来的破土动工所积累的
罪业:上游的罪业吗?我们的大地法死了。
不,我并不会夸张到,把那只鬼球当作
大地法的幽灵。除了愚蠢,它什么也不是。
但有时,它也拒绝着把全世界都当成一张
台球桌的跨领域游戏者们,拒绝着你们和我。”
“我们没有证据。关于地理黑洞
我们永远不会有充分证据。能够
组织和垄断证据的人不会是我们
但是会凌驾于我们,从而解释我们的现实。
因此,就在每次灾难中,我们也失去了现实。
因此,灾难被称作灾难,正是因为
那随死亡而轰然发生的——不可研究性!
正是因为,死于其中的一切立刻成为
不可研究的!那些有可能告诉我们灾难中的
生命是什么的一切,永远、永远死灭了!”
“死去的事物就这样打断了我们。
大地的死亡凝视造成的人民惊恐
与官方惊恐,被进行‘最快捷修补’③
(是的,这是你的阿什伯利的题目),在一项项
重建工作中。可是,被称之为‘废墟’的
正是因为那轰鸣着的、让你我的语言
就此毁碎的不可研究性,才成为废墟!
让事后的理解统统成为一种下游的讨论。”
“唉!唉!难道废墟不是一只大球吗?”
——他越说越激动。我不知道他的话
掺杂了多少的知识,多少的无知
总之,以我国乡土艺术家那种急吼吼的
前沿跟随者的方式,混合了有趣与胡扯。
但还不算是随便看不起常识,这大概是
因为,毕竟,他忠于那只死后成圣一般
兼做愚蠢之神和水神的球,这使他
管住了自己的嘴,不会把话
越说越蠢当作是越说越激进
他知道,那无异于在球中的
彼此呕吐。所以,这也算是
令人愚蠢的,也令人有所知。
接下来的奇谭宏论,读者
任您评判。如果我必须选择
我愿意做一条客船上的乘客
因为,我喜欢以正常的方式
而非走一条称作非常的捷径
在他如下描述的山河中悠游。
“兄弟,难道我们不是乘着
一块大废墟,在到处漂流吗?
我们的大废墟也一蹦一蹦地
漂浮在这个世界紊乱的水流中
仿佛弹跳在魔鬼的羽毛球拍上
它玩弄着我们,但是为什么
不把我们击出呢?我们会被
击向什么?而这就是那只球
赋予我们的视力,请看——
这幅画面:我们的大废墟在
当代乱流中蹦蹦跳跳,那只球
也在我们身后蹦蹦跳跳。我劝你
钦佩格雷伯不如做回你的格列佛
在这浩瀚的黑暗水体之上,重写
你的飞岛,你那些大人物的城邦
和小人之心的共和国,尽情嘲讽
他们用新工具描画的各种海洋和
陆地上的发展蓝图。但水无定势
兄弟,难道你不也曾在无人区
寻找水体存在过的一点痕迹吗?
它们总是消失在荒漠,又猛然
摆动,像耶梦加得昂起头颅。④
所以,你可以在濒临枯竭和那种
狂乱的摆动之间,找寻你的语言
而那只球,像一只抹去了你的
知识的橡皮擦,把你变成一个
反向的绘图员,你写下的一切要么
消失,要么就如同泥沙俱下的鞭笞
这样,没有主人的大废墟才是
可见的!这样,不可被你们的
任何想象叠加在它之上的大废墟
才会成为这个世界的反像地理!
才会成为拒绝被造型,拒绝拟像的
大地法!忘了那些靓丽的可见性吧
无非是《话说长江》的新浪潮版本。⑤
无非是掩盖了那作为共同尺度的
废墟,而是让我们看到了造型!
是废墟,在把四分五裂的我们整体化了
我们的命运在其中翻滚,我们的灵魂
在其中作呕。我们走出了那只橡皮球吗?”
他见我听得出神,于是又重复一遍
这使我感到他即将结束发言——
“我们走出了那只橡皮球吗?
显然没有。但是,我们可以
找到把自己变成球中之球的方式,
变成愚蠢中的愚蠢,翻滚中的翻滚
从而继续一场没有结束的漂流。
而你,也正好得到成为诗人中的
诗人的机会。就把这只鬼球带给
你虚伪的同类,你的读者。与其说
让它回到他们的知识,不如说回到
他们的翻滚,由此回到汪洋大海般的
无知,大脑内部翻滚着大脑的……宇宙。”
我昏头昏脑,听完一个从对我的否定开始
经过一只幽浮的橡皮球,再到大地法是怎样
闹鬼的鬼故事。我是该严肃对待,还是逃走?
这是一个疯了的略萨送给我的中国套盒吗?⑥
总之,这愚蠢套住愚蠢,大脑套住大脑的
中国套路,使我所知的一切变得颠转不定。
此时此刻,我的同类正在研究欧亚折叠
和无限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多样化方式。
那只鬼气森森的球,是否也跟着他们
开始一场量子漂流?即使我并不相信他
但我知道,我仅有的一点知识完全可以
反过来,把高大上的一切都变成高康大。⑦
此时此刻,我没有感到烦乱而是快活。
此时此刻,我在基建蓬勃、桥梁宏伟
人民好吃好喝,因此重力正常的贵州。
2020.10.
__________________
①《在黄昏弥漫的天空中》是约翰·阿什贝利诗集《山山水水》里的一首长诗,用接近 150 行的诗句将包括黄河和长江在内的几乎所有世界著名大河联在一起。
②敏希豪生男爵是德国作家拉斯培和戈·比尔格编写的故事《吹牛大王历险记》的主角。
③“最快捷修补”也是约翰·阿什贝利一首诗作的标题。
④耶梦加得(Jormungand、Jörmungandr),北欧神话中环绕人世的巨大海蛇。
⑤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及人文的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于 1983 年 8 月 7 日首播后,成为上世纪
八十年代最受欢迎的电视纪录片。
⑥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文版曾以《中国套盒》为书名。
⑦高康大是拉伯雷《巨人传》的主角,其子是庞大固埃。

《希望日记》之二、没有世界的世界主义者
2020年春季的一天,听到Zbigniew Preisner的组曲《希望日记》(“Diaries of Hope”), 使我产生写同题组诗的念头。之后,10月,三位艺术工作者,江萌、郝敬班和苏伟给我他们发 起的一个艺术项目的介绍,其中,他们写道:“BLM、白俄罗斯人的抗争、经济危机——面对这些 紧随新冠疫情发生的流动的事件,我们无法辨认旁观者、参与者、目击者、施害者和受害者—— pandemic(瘟疫),在它希腊语的词源中,正是‘所有人’的意思。我们又渴望可靠的信息和知 识能帮助我们理解发生的事情,但又对自己或者他人经验的信任完全动摇。疫情好像一夜间把关 于世界的知识变成了废墟。”而这项工作,意在“通过邀请更多的、不局限于艺术行业的人不断 参与……呈现某种身处在某一事件、革命或者运动中的感知,一起成为这个项目的共同发起者和塑造者。”他们问我,是否可以为他们写点什么,于是我着手写这组诗。完成时,已过去半年。虽是为三位朋友而写,但素材与构思并不囿于他们的项目介绍,而是在主旨上与之呼应。《没有世界的世界主义者》是这组诗的第二首诗。《希望日记》由五首诗组成:1,《绪言》;2,《没有世界的世界主义者》;3,《疲倦的运动的儿女》;4,《回顾2000年—2020年间的死亡》;5,《一封致恩斯特·布洛赫的信》;6,《墓志铭》。
“您这篇‘绪言’堪称颇有特色,但是我
就想问问你,你来自哪儿?你来自什么?
因为,每个你这样的野路子都可以还原为
外省的可疑分子,令我厌烦的是,为什么
总是有你们这些人。是的,你们太多了。”①
这半人半鸟的还原主义批评家
一边在黄昏中盘旋,一边对我说:
“就像在《伊利亚特》中,也在大凉山
你都遇到的那样,不如直接报出你的家支
说出你的来源,你跟哪些人是一伙儿的?
你的专业是什么?往往就是你们这种人在破坏
这社会支柱般的树形结构,通过文艺手段
把你们的来历不明进行历史化。说白了
成为一种保留个人解释权的左派,是你们
唯一的选择。因为你们其实无路可去,这个
社会的善恶树上,没有给你们吃的果子。
所以,你们自己开荒种植的那些杂交品种
那些非法出版物,自导自演的贫穷戏剧
又是些什么?没有谁需要这样的禁果。
能够被敌人吃下的,才是真正的禁果。
但你们的生命,却参与浇灌着
你们的敌人以之为生的禁果。
你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构成什么前线
只是你们确认自己活着的底线。如落叶
飘零的是你们,是的,荷马会为你们歌唱
没有荷马,你们就自己发明荷马
但别忘了,荷马是个瞎子,他在这棵
世界巨树之下,盲目地清扫着许许多多
像你们这样的人。所以,每个民族
都有一个名叫‘荷马’的
收尸人般的环卫工。
但你们不再年轻,这些
文化幻想只带来痛苦,而非希望。
你最好在有生之年实事求是,抓紧
时间坦白,既然你我都厌倦了那种
无关实质的开明风度,它比否定你们
更曲解你们,所以直接点儿,你们究竟
想做和还能做的是什么?既然你认为
你也是人文主义者,这意味着你也接受
传统价值,那么,请告诉我,你的
那个世界,是成长论还是突变论的?”
就这样,它讯问着我。这只老鸟
想要一举让我这样的人变得简单化。
我该对这只宣称反对突变论的
突变物种,说些什么?我看着它那
并非以狮身鸟翅,而是以熟人面孔
拼凑成的非人形象,回答它:
“是,我是成长论者。
但我相信有一种成长被打断了,
来自各个大陆上的历代迁徙者
来自内在的非洲和内在的亚洲
来自不论任何肤色的人皆可铭记的
内在的高加索与地中海,来自
内在的帕米尔和天山,阿尔泰
和戈壁,内在的蒙古高原和楚科奇海
来自每个‘黑格尔世界之外的世界’②
来自不论任何肤色的人身上的
内在的黑人,内在的印第安人
内在的鞑靼人,来自我们身上的
内在的藏族人、苗族人和彝族人
来自那些在每处海岸、每个山岭都可以
自由交谈的人的多重世界,它的成长被打断了。”
“不”,它说:“不,多元主义的
民俗故事,并不能帮助你们这些
无身份人士改善被边缘化的处境。不能。
地方性太多了!世间之道
已经改变,就连世界文学
也更新了识别系统。请问
你怎样把你平凡的‘人民’和
你讨厌的‘庸众’区分开来?
你怎样‘站在人这边’却又
保证他们中没有‘末人’?
难道你不是也同意,人与人的
区别常常大于人和猴子的区别?
难道如今不是一个对人的定义
和种类进行再区分的巨变时代?
香港、新疆只是它的派生现象
它们过时了,它们已成为世界的
外省,因此才进入了你的语言。
你也过时了。一切与你知道的
正好相反,如今,世界革命者
是你们反对的人,而不是你们。
你的外省故事也只是过时的人
走向消亡的缓冲形式。你以为
你从它们,听见了那些拒绝产生
社会形象的原点的微弱呼吸。小心
你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变着法儿
一遍遍回到那个母题:等待野蛮人。”
我感到恶心。恶心于它洋洋得意
却又并不直接显得战无不胜,以一种
并不会吃掉回答错误的人的表情
像文明办案那样学会了文明盘问。
但是,与其说它的问题过时了
不如说,对于回答是否正确
它已无决定权。而且这只老鸟
并不会为任何一句正确回答而死
盘问别人,只是它死皮赖脸活下去的方式。
于是我说:“别把他们放在‘世界’这座
天平上称量,别比较他们,你没有
那样的天平,但你总是显得你有。你站在
你的世界的门前,就像对着那个注定要去
成为下一代统治者的二代那样,吓唬他。
你最错误的是认为,我们想要从你说的
那棵树上摘取什么,不,我们想要
纵火点燃那棵树,让它成为生命树。
(既然你提到荷马,就让他做烧火工。)
我们想要成为火焰本身,想要成为
一棵火树,烧毁你们的种子和根须。
只有一个积极意义体系的生长才能
使大地值得生活,我们的实事求是
就是参与明确一个不灭的希望图像。
我们一遍遍回到的母题,是爱。”
“还以为你能讲出一个不同的故事。
爱。真叫人失望。爱。
难道,你罗列那些地名人名
以爱的名义,去写他们的故事
不是也在挖取他们的希望图像吗?”
“不,我们都在失去。我也在失去。
因此我们才互相给予。
因为你的世界的存在,才使产生
他们这样的人的能力被截断了。
但是,没有他们这样的人,就不再有世界。
在漫长岁月中,他们中的一些人
不懈工作,平静于不为人知
和不被理解,仿佛没有世界。”
“那么,他们是什么?
没有世界的世界主义者吗?”
“这是你的最后一个斯芬克斯问题。
他们不会为任何一头斯芬克斯停留
而是从你粗鄙的谜语中,救走
人之谜,就像往未来安放一个孩子。
对于他们的生命,不论你,还是你的
任何一种色厉内荏的变种,都无从置喙。
是的,尽管我不能与之相比
但我来自他们。他们就是你这种
说话离不开否定的阴阳怪气者的
简单反面,在平平无奇的地方
做着平凡的事,只为有益于他人。
他们就是那些在中国深处积极生活的人。
他们,就是那些在没有世界的
世界深处,保持肯定性的人。
现在,谜语该改改了
我问你猜:早上是一把手
中午两手都要硬,晚上是
看不见的第三只手,这是什么?”
但是,这只无赖的老鸟并不回答
而是端着一副黄昏才起飞的架子
不再理睬我,消失在北京的雾霾中。
2021.3.
__________________
①“你们太多了”,化用自哈代。《无名的裘德》里,裘德的 11 岁的长子(绰号“小时光老人”) 认为自己和弟妹三人是父母的累赘,杀死弟妹后自己也上吊自杀,遗书中写道:“我们太多了”。②“黑格尔世界之外的世界”是库尼亚《腹地》中一个章节的标题,概述巴西地理。